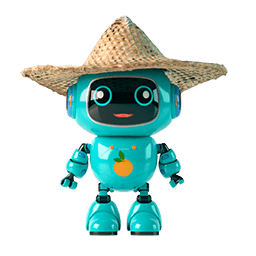乡村不是“退路” 且看数字游民与“新事业”
--
2022年10月,记者在浙江安吉溪龙乡的DNA数字游民公社住过一周,第一次深度接触国内的数字游民群体和他们的社区。那时,“数字游民”在社交媒体已频频出现,不少人好奇并羡慕这种看似自由的生活状态。
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从城市来到乡村的目的各不相同。一部分数字游民和乡村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将乡村视为“新事业”。
基层政府敏锐地嗅到数字游民对中国乡村的价值。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上海金山、浙江安吉、浙江丽水、江苏扬州、安徽黄山、四川资阳、海南海口等十余个省市,都推出相关的扶持政策。政府青睐的背后,是中国乡村对数字化人才的渴求。
问题随之浮现:数字游民通常为了体验不同风土人情而频繁更换居住地。这群流动性强、热爱自由的数字游民,如何才能真正参与中国乡村建设?又会遇到哪些“水土不服”的困境?
乡村不是“退路”
孙启超不会想到,原本在大城市工作的他,如今会在黄山黟县三合村,给村支书拍短视频。
两年前,他从一家教培公司辞职,来到DN黄山数字游民公社。在他看来,乡村不是“退路”,而是“机会”。“如今年轻人开始‘规模返乡’,年轻人越多的乡村越有发展潜力。”孙启超和当地人交流发现,“机会”就藏在他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比如茶叶,“当地人不觉得是资源,但我相信原产地的农产品一定能讲出好故事”。
孙启超将自己打造的一门有关短视频变现的课程无偿分享给社区里的数字游民。95后驻村干部小鹏得知后,邀请他给村里拍短视频。两个年轻人的合作就此开始,不仅给村支书拍短视频,还给当地茶叶做品牌设计和运营。
三合村以茶叶种植为主要产业。以往农民将加工后的茶叶统一卖给收购商,缺乏市场话语权。如今,孙启超带着大山里的茶叶走向各大展会,售价比农民直接卖的价格提升至少15%。
黟县现有5家不同主题的数字游民社区,还设立了数字游民工作专班,出台《支持数字游民共居共创政策10条(试行)》,希望招引更多数字游民前来。第一步是激活“流量”,形成集聚效应,拉动文旅消费;第二步则希望把“流量”转化为“留量”,让外来人才扎根,与地方产业共成长。
可数字游民的强流动性,让基层政府感到棘手。孙启超就常被基层干部问起,“如果你们走了,项目怎么办?”“我们肯定是会走的。”孙启超如实回答。
一位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干部表示,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对当地产业和乡村建设推动有限,部分数字游民社区设施完备却缺乏人气,与当地缺乏互动。“这些都不是基层政府所期望的。”
乡伴文旅集团创始人朱胜萱有近20年乡村运营经验。他在江苏昆山的计家墩理想村设立了数字游民社区。如今的理想村已有不少民宿主扎根,但朱胜萱认为,他们为乡村带来的活力到了瓶颈期,他希望数字游民能带来新的产业发展机会。
一名AI从业者想在村里举办“黑客松”培训项目。该项目需要从业者在短时间内通过团队协作编程,开发创新项目。乡村宽松的环境正好适合短期集中创作。目前,培训已举办两期,均是依托数字游民引入的资源。第三期正在筹备中。
人才“扎根”执念
“工作的持续性不在于某个人,而在于不停有人做。数字文明时代的人才要像河流一样流动起来,但河流从不缺水。数字游民给乡村带来的机会、资源和影响力,在政府考核体系中无法被评估。”朱胜萱直言。他将数字游民比喻为“一种深度的乡村人才振兴模型”。他曾与不少基层政府对接,发现对方虽对数字游民感兴趣,可在落实过程中却阻力重重。
最大的阻力在于长久以来对人才“扎根”的执念。传统思维习惯将长期驻村者树立为典型,好像只有“留下”才有价值。但在朱胜萱看来,当下中国乡村正是因为人才从城市到乡村的单向流动,出现诸多发展难题。反观城市,人才流动是常态。乡村亟需多元化人才,数字游民群体是其中一类。
“扎根”执念源于基层政府在人才引进与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硬性指标要求,而数字游民作为流动人才,其“不确定性”与政府诉求之间存在天然矛盾。某乡镇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坦言,起初他们对数字游民进村并不看好。游民社保大多不在当地缴纳,创业成果也未必在当地转化,人才引进指标仍需靠第三方公司达成。
在政府的考核体系里,传统招商引资模型以企业数量、投资金额、税收创造等为指标,民宿、康养、文旅等常见的乡村产业均契合该体系。然而,数字游民多无公司主体,难以纳入考核。“考核问题不解决,数字游民为政府带来的只有影响力,难助力实际发展。”朱胜萱说。
尽管各地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数字游民的人才扶持政策,但游民们“体感”不强。乡村人才政策的吸引力远比不上一线城市。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指出,当前地方政府仍沿用传统人才引进模式,将数字游民视为借助互联网创业的青年群体。实际上,“有人才”与“有人才持续驻留”是不同概念。现有人才政策多是统一方案,缺乏针对数字游民这一新型人才的细分设计。她建议,倘若有意探索以数字游民赋能乡村发展的创新模式,地方政府可考虑进一步细化人才政策,秉持“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理念,挖掘数字游民为乡村带来的独特价值。
国内一高校调研团队曾给想要吸引数字游民的基层政府提建议,基层政府要实现长久留人,关键在于提供优质服务。数字游民自发在乡村开展活动的同时,基层政府可从中筛选优质项目进行孵化,推动其与本地产业紧密结合。
为适应数字时代人才流动的特性,多方主体都在探索。黟县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数字游民在当地的停留时间多在半个月至3个月。起初,他对如何围绕短期停留群体开展工作也有困惑。如今,黟县通过产业联结机制破题,借助全国性人才生态系统“游牧岛”线上平台,与数字游民达成合作。
据介绍,该平台由NCC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搭建,且平台内链接入驻了全国多家数字游民社区,注册的游民人数达十万人。若当地产业发展有需求,政府可在平台上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发布任务。目前通过这一机制,已策划实施活动项目18个,完成“揭榜挂帅”任务22个,兑现资金54万元,带动“五黑”产品、稻田咖啡等销售额超600万元。依托互联网开展工作的模式受数字游民去留影响小,游民们也可持续赋能乡村发展。
好社区是“入口”
大多数数字游民会选择稳定的社区驻留。对基层政府而言,社区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才聚集体,比分散的个体更适合成为开展人才服务与产业对接工作的抓手。
深圳大学一学生团队曾做过有关数字游民社区的田野调查。他们依据不同的发展模式,将数字游民社区划分为“自然生长的原生态社区”和“政府主导下的社区”。
在云南大理,政府的支持相对有限,也未设置考核指标,数字游民自由发挥才能,为乡村发展注入动力。而在部分地区,基层政府大力介入数字游民社区建设,却往往导致社区发展偏离初衷。
原本以自由、灵活为特点的游民生态,被纳入传统招商引资模式。朱胜萱观察到,许多社区起初是松散的游民集合,但在政府的推动下变成打着数字游民旗号的“人才孵化器”,住的也不是真正的数字游民。
过度介入引发游民不满。他们需耗费大量时间应付各种视察。有人反映,晚上9点还有领导视察,工作人员甚至直接进入游民宿舍。
记者询问一些基层干部如何理解“数字游民社区”。有人回答,“就是个民宿”,似乎将“社区”的概念简单化了。而与多位游民深入交流后,记者发现,他们最初奔赴乡村,是被风景和物价所吸引,而真正让他们愿意长久留在乡村的,是在社区里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在中国,大部分数字游民倾向于“抱团取暖”。因此,社区不仅是民宿,更应是一个承载着深度人际关系的空间。国内较为活跃的数字游民社区,都注重“社群”打造,以“生态思维”构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既需要时间的沉淀,也充满变数。
许崧是国内最早涉足数字游民社区创建与运营的实践者之一。三年前,他前往浙江某地谈合作,当地领导计划将闲置空间改造成数字游民社区,询问他需要提供哪些支持,但这场合作最终不欢而散。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基层政府大多秉持目标导向思维,期望得到可预期、可量化的结果。但搭建以“人情”为基础的社区,能留住多少游民本就是未知数。
当然,也有基层政府意识到这是个转化率问题。在筹备DN黄山数字游民公社时,当地政府明确表态,“这是我们给黄山买的一张彩票”。许崧说,虽无法保证所有来到社区的年轻人都能扎根,但只要社区搭建得好,总会有人选择留下,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数字游民和返乡青年不同,不是本村人。如果社区无法带来舒适感和获得感,他们也就打打卡再离开。因此,好的社区是一个‘入口’,让游民愿意低成本在乡村生活一段时间,熟悉周边环境,结交新朋友,增强他们与乡村的黏性。”
如今,越来越多基层政府意识到,相较于政策,社区的运营状况才是决定游民停留时长的关键。因此,专注于数字游民社区运营的第三方企业越来越多。然而,运营团队的理念与政府诉求之间尚需磨合。如何平衡运营团队的特色与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经历“再社会化”
即便政府通过搭建线下社区或线上平台尝试与游民合作,在具体项目中,阻力依然存在。
孙启超刚到村里时,接不到适合的政府项目。这类项目往往资金不多、限制不少。以短视频拍摄为例,对方要求成品需确保一定的播放量,而在业内,播放量可以购买,一旦有了硬性要求,创意和才华反而不是刚需。在孙启超看来,有想法的年轻人对此不会感兴趣。
即便接下项目,也面临着高昂的“沉没成本”。多位游民提及,尽管他们积极承接乡村建设项目,但沟通时常不顺利,经常遇到项目在任意阶段被叫停的情况,前期投入也付诸东流。“钱少、限制多、考核僵化”,数字游民认为,这一考核机制违背了创意工作的规律。
另外,政府与陌生的游民群体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孙启超曾询问村干部,黄山有这么多游民及社区,为何选择与他们合作?对方的回答是,“有些社区想直接获利,收钱干活。”也有基层干部认为,政府和数字游民合作的前提是,游民先要做出成效,而不是一味索要资源。
自从团队和三合村合作后,不少村子也向孙启超抛来橄榄枝。他发现,每次政府在介绍他们是数字游民后,都会补上一句,“这个团队做了三合茶”。孙启超感慨,真正想在乡村有所发展,不是靠“数字游民”的热度,而需要靠项目正名。前期必然需要投入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让政府看到数字游民的能力。
“政府和资本更倾向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一些数字游民对此表示无奈。朱胜萱建议他们换个视角看问题,数字游民得做符合市场规律的事,后续支持才会水到渠成。若一开始就指望外部支持,反而说明模式不可持续。
不过,孙启超还是希望基层政府偶尔能“雪中送炭”,“尽可能释放项目,供数字游民实操。项目考核可以更灵活,接纳创意和一定的容错率”。
唐丽霞指出,数字游民作为新生事物,融入乡村发展面临诸多适配问题。乡村社会与城市有截然不同的运行规则,政府工作逻辑和企业模式也差异显著,数字游民到乡村需经历再社会化过程。本地政府和社区可提供针对性培训,帮助数字游民了解政府运作机制、行政管理要求以及乡土社会特点,提升其适应乡村环境的能力。
正在“双向奔赴”
数字游民入驻乡村后积极构建自身业态,乡村则为其业务拓展提供广阔空间。他们凭借创新活力与数字化技能,反向驱动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黟县数字游民工作专班的基层干部介绍,当地人口约7万人,文旅资源丰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不少,但多是做餐饮和民宿,业态较为单一。黟县政府希望更有创意的年轻人能在自媒体内容创作、农产品品牌营销等领域发力,赋能乡村发展。
这些领域在市场上已有成熟服务体系,数字游民并非专业对口、具备完整服务能力的主体。可现实是,受制于资源对接的壁垒,乡村往往无法触达专业公司,即便能触达,也负担不起成本。以三合村为例,孙启超了解到,村里每年用于乡村建设的相关补贴款项仅为10万元左右。
相比之下,数字游民灵活且技能多元,组成的团队兼具多方面能力,不像企业那样有固定运营成本和高服务费,更愿意以较低成本为乡村农产品提供定制化服务。
许崧认为,数字游民以个人为单位,凭一台电脑就能工作,是典型的单兵生产模式。在社区里结识伙伴后,他们便临时组队,形成一种灵活协同的“海盗船”式关系——因项目而聚,结项后自动解散。如今,在许崧参与建设的安吉和黄山的数字游民社区里,这样的“海盗船”越来越多。他们的项目不仅来源于城市,也来源于乡村。
朱胜萱说,并非所有乡村都适合打造数字游民社区或发展数字产业。实际上,数字游民更适合推动已有一定基础、处于发展瓶颈期的乡村进一步发展。这些乡村大多分布在大城市周边,虽基础设施完善,但在人才吸引和产业发展上仍显乏力。
当然,一些“双向奔赴”已在悄然发生。为了加强本地青年与数字游民的联系,黟县与数字游民社区合作开办黟县青年夜校,通过体系化课程,满足本地青年技能提升需求。孙启超也曾受邀给村支书和驻村干部讲授电商运营和短视频拍摄课程。
“数字游民本质上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次重新选择人生路径的机会。目前国内这一群体的总体规模趋于稳定。当前,数字游民助力乡村振兴在中国尚属新颖模式,全国层面尚未出台针对性政策,各地正积极开展不同模式的探索实践,成效仍需观察。待模式成熟后,数字游民或许会被归纳为一种特定人才类型。当下,数字游民与政府都处于摸索阶段,需共同探索契合双方需求的发展路径。”唐丽霞说。